很多人認(rèn)為,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制造取得的成就,特別是民營企業(yè)家獲得的成就是由于享受了時(shí)代的紅利:大規(guī)模市場(chǎng)、廉價(jià)勞動(dòng)力、低成本環(huán)境成本等等。這種說法很難說是錯(cuò)誤的,但卻不是最為關(guān)鍵的,因?yàn)檫@種紅利對(duì)于所有經(jīng)濟(jì)主體、所有時(shí)代都是一樣的,包括外資和那些倒下去的企業(yè)家們,以及根本不取用這些紅利的人們,而且這種紅利是一種歷史的自然狀態(tài),之前也一直保持自然的存在。
在我看來,中國制造業(yè)的崛起源于創(chuàng)造的基因,而非自然的紅利。創(chuàng)造的基因始于中國企業(yè)家們饑渴般的學(xué)習(xí)。
基因一:饑渴般的學(xué)習(xí)
喬布斯對(duì)于蘋果價(jià)值觀的描述:Stay Hungry,就是永遠(yuǎn)保持饑渴的狀態(tài),而中國制造業(yè)的很多企業(yè)家們絕大部分都有這種根深蒂固的基因,因?yàn)樗麄兩钌畹闹溃绻粚W(xué)習(xí),甚至如果不瘋狂的學(xué)習(xí),就跟不上這個(gè)時(shí)代,就隨時(shí)可能被淘汰,尤其是改革開放后走上時(shí)代舞臺(tái)的第一代企業(yè)家們,他們大部分都沒有受過良好的、系統(tǒng)的教育,面對(duì)羸弱的制造業(yè),見到了歐美發(fā)到國家的強(qiáng)大制造業(yè),對(duì)于這之間的差距有切膚之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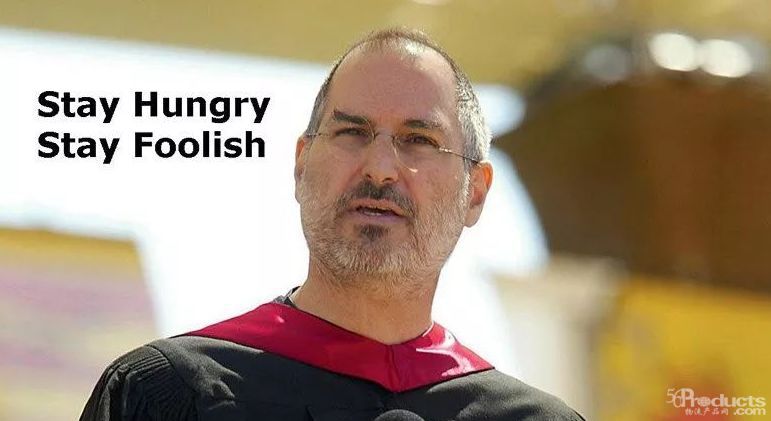
2000年前后,任正非到美國考察,到IBM參觀,一下子就被IBM高效而強(qiáng)大的研發(fā)管理系統(tǒng)驚呆了,他知道這是正規(guī)軍和游擊隊(duì)的距離,下定決心,無論花多少銀子也要學(xué)會(huì)這套管理模式,IBM從來沒有想到有人學(xué)這些,更沒有想到是中國的一家小小的民營企業(yè)來學(xué)習(xí),于是給任正非一個(gè)價(jià)格:300美元到680美元不等。大家一聽到這個(gè)價(jià)格覺得也太便宜了點(diǎn),答案是NO,IBM當(dāng)時(shí)給華為派了70名顧問,這些顧問每小時(shí)的收費(fèi)是在300到680美元不等,這對(duì)當(dāng)時(shí)的華為可謂天價(jià),而且他們?cè)谌A為一呆就是5年時(shí)間。據(jù)統(tǒng)計(jì),這套研發(fā)管理系統(tǒng)讓華為花了足足20億人民幣,這是什么概念?這幾乎是當(dāng)時(shí)華為一年的收入!很多人,估計(jì)包括IBM的人,都覺得任正非夠傻的,連個(gè)價(jià)格一分錢都沒有還。今天,還有誰認(rèn)為當(dāng)年的任正非“傻”呢?如果沒有這傻傻的學(xué)習(xí),怎么會(huì)有今天的華為?
我有一位企業(yè)家朋友,是江蘇電纜領(lǐng)域的佼佼者,這家企業(yè)最早是一家中日合資企業(yè),雙方各占50%股份,使用日本品牌,因?yàn)槟莻€(gè)時(shí)候“日本制造”絕對(duì)是品質(zhì)的通行證。在高層管理方面,日方?jīng)]有派一堆人,而是只派了一位總經(jīng)理過來,具體技術(shù)和生產(chǎn)環(huán)節(jié)倒是相繼派人進(jìn)行指導(dǎo)。2012年前后,合資到期,日方準(zhǔn)備撤走,企業(yè)品牌也不能再用日本品牌,只能用中方品牌;日方總經(jīng)理臨回國前,中方為他餞行,請(qǐng)他吃飯,結(jié)果,這個(gè)日本人吃飯時(shí)酒喝高了。酒后吐真言:“咱們一起工作將近20年,今天我該走了,告訴你們一件事,當(dāng)時(shí),我被派到中國來的時(shí)候,問上司到了中國企業(yè)應(yīng)該怎么干,上司很神秘的說:啥也別說,啥也別干!他心想,這是啥指令啊。到了中國企業(yè)以后,他明白了上司的意思,就是不要主動(dòng)讓中國人學(xué)技術(shù)”。他回日本幾年后,退休了他回到中國看望這家企業(yè)的時(shí)候,被驚呆了:離開日本人的管理和技術(shù),這家中國企業(yè)干得比以前還要好得多,規(guī)模也大了不少,其中國本土品牌也已經(jīng)成為業(yè)內(nèi)的知名品牌。他盡管很友好,但是內(nèi)心還是認(rèn)為,這家企業(yè)離不開日本人,結(jié)果發(fā)現(xiàn)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看到他的表情,中方老同事們都開心的笑了:日本人在這的10多年里,我們好好的當(dāng)好學(xué)習(xí),利用一切機(jī)會(huì)、一切方法、一切時(shí)間去學(xué)習(xí),因?yàn)槲覀冎溃毡救丝隙糁皇郑挥星Х桨儆?jì)的學(xué)習(xí),才能獲得真正的能力,才能受人尊重。
在制造業(yè)內(nèi),像這樣狂熱學(xué)習(xí)的例子很多很多。這正是中國制造崛起的第一個(gè)基因。
基因二:勤奮致富
可能是歷史上見慣了天災(zāi)人禍,中國人的生存意識(shí)極強(qiáng),勤勞的品質(zhì)全球公認(rèn)。華人走到哪里,不管面臨怎樣惡劣的環(huán)境,都能夠生存下來,而且生存的很好,往往會(huì)成為當(dāng)?shù)叵鄬?duì)富庶、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族群。依靠勤勞致富,這可能是中國人祖祖代代傳承下來的基因,正像國家領(lǐng)導(dǎo)人提到的“對(duì)美好生活的向往”是中國人的共同追求,而且這種追求是靠勤勞獲得的,中國人歷來有“吃得苦中苦,方為人上人”的古訓(xùn)。

有一次,在德國的慕尼黑與一位德國朋友聊天,談到中國人與德國人的比較,我說:在中國人的眼里,德國人勤奮、敬業(yè)、遵守規(guī)矩,就像工作機(jī)器一樣。結(jié)果,德國朋友聽了以后,哈哈大笑:周博士搞錯(cuò)了,跟中國人相比,德國人哪里像機(jī)器人,中國人可以自覺工作十幾個(gè)小時(shí),而且連續(xù)多年如一日,德國人一天工作八小時(shí),一分鐘都不多干,中國人太勤奮了,德國人根本競(jìng)爭(zhēng)不過中國人。
我相信,正是這種勤勞致富的品質(zhì)和追求,才涌現(xiàn)了一批有一批的創(chuàng)業(yè)者,才產(chǎn)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優(yōu)秀企業(yè)家,也正是這種追求,這批優(yōu)秀的企業(yè)家才能在遇到困難的時(shí)候,不后退、不逃避,而是迎難而上,堅(jiān)持到底。我在嘉善看到了一位70后的汽車零部件企業(yè)老板,年收入超過3個(gè)億,毛利超過了30%。一種普通的汽車零部件,怎么會(huì)有這么高的毛利?等我知道了他每天(不分節(jié)假日)都要工作12個(gè)小時(shí)且沒有啥娛樂愛好的時(shí)候、看到了他那分散在三個(gè)地方的簡(jiǎn)易車間和簡(jiǎn)陋的辦公樓的時(shí)候,其實(shí)心中就有了答案。當(dāng)他的朋友說:他現(xiàn)在開的這輛寶馬也是在他不斷說服下今年剛剛買的,好幾年都開著一輛破爛不堪的舊車亂跑。當(dāng)他的朋友說“你手里存那么多現(xiàn)金干啥,投資點(diǎn)的吧”,他的回答是“我只會(huì)干這行”。這樣的企業(yè)家,我在蘇浙以及山東一帶遇到很多很多。如果他們都像歐美企業(yè)家那樣講究,都像某些國內(nèi)其他行業(yè)的大佬迷戀炫富、那么嘚瑟,如果他們也應(yīng)該度假就度假、應(yīng)該休息就休息,他們哪里會(huì)有今天?難道他們笨嗎?他們往往非常聰明且專業(yè),他們和普通人最大的不同就是罕見的勤勞和專注,以及常說的“苦逼一樣的自律”。
這正是中國制造崛起的第二個(gè)基因。
基因三:敢于創(chuàng)新
制造業(yè)是不可能依靠自我封閉發(fā)展的,只有創(chuàng)新才是唯一正道,而中國制造的成長(zhǎng)恰恰就是創(chuàng)新的推動(dòng),這里有“敢為天下先”的創(chuàng)新思維、有“不求所有,但求所用”的拿來主義創(chuàng)新,也有“沒有條件,創(chuàng)造條件也要上的”不甘服輸?shù)募夹g(shù)創(chuàng)新,也有“沒有做不到,只有想不到”的客戶需求模式創(chuàng)新。

曾幾何時(shí),德國社會(huì)學(xué)家馬克斯?韋伯在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一書有一個(gè)觀點(diǎn):新教精神及其形成的倫理是西方資本主義創(chuàng)新機(jī)制的根源,同時(shí)也得出了另外一個(gè)結(jié)論:東方的儒家倫理可能是東方不能誕生資本主義的精神根源,而且對(duì)現(xiàn)代社會(huì)的創(chuàng)新會(huì)產(chǎn)生阻礙。這一觀點(diǎn)的提出似乎解釋了西方資本主義工業(yè)化創(chuàng)新的崛起以及東方為什么不能誕生現(xiàn)代工業(yè)創(chuàng)新體系。其實(shí),這是典型的事后諸葛亮總結(jié)式分析。英國歷史學(xué)家馬克?泰勒在他的著作《為什么有的國家創(chuàng)新力強(qiáng)》談及20世紀(jì)70年代英國歷史學(xué)家卡德韋爾闡述的一個(gè)定律:從數(shù)千年的歷史看,一個(gè)國家的創(chuàng)造力只能維持短暫的時(shí)期。幸運(yùn)的是,總有國家接過創(chuàng)新的火炬。作者進(jìn)而認(rèn)為,這一現(xiàn)象其實(shí)與國家體制沒有什么直接關(guān)系,創(chuàng)新更重要的推動(dòng)力是“國家不安全感”,因?yàn)樗呀?jīng)發(fā)現(xiàn),從幾千年的人類看,創(chuàng)新可以發(fā)生在任何一種體制中間,只要這種體制活力充沛,有一種生存危機(jī)意識(shí),就是所謂的“不安全感”,而中華民族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意識(shí)體系中,“居安思危”恰恰是其最低層的邏輯。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繁衍數(shù)千年,中華文明之所以沒有出現(xiàn)斷裂,與這種根深蒂固的危機(jī)意識(shí)有關(guān)。而上世紀(jì)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全年釋放了民族的這種危機(jī)意識(shí),刺激了我們的企業(yè)家群體“只爭(zhēng)朝夕”、“數(shù)風(fēng)流人物,還看今朝”的創(chuàng)新意識(shí)和創(chuàng)新行為。
這一基因,仍然是中國制造業(yè)企業(yè)家在新時(shí)代取得新成就的基礎(chǔ)推動(dòng)力。
讓這個(gè)社會(huì)珍惜中國民營企業(yè)家吧,他們是勞動(dòng)者中的佼佼者。
以下文章來源于國裝智庫 ,作者周永亮
國裝智庫:國裝智庫是由國家級(jí)裝備制造業(yè)首席智庫----國資委機(jī)械工業(yè)經(jīng)濟(jì)管理研究院聯(lián)合一批裝備制造業(yè)領(lǐng)域的資深專家、行業(yè)領(lǐng)軍企業(yè)、大型投資機(jī)構(gòu)共同發(fā)起成立的先進(jìn)制造業(yè)與裝備制造業(yè)智庫平臺(tái)。
新時(shí)代鞋服物流與供應(yīng)鏈面臨的變革和挑戰(zhàn)03月07日 20:38

點(diǎn)贊:這個(gè)雙11,物流大佬一起做了這件事11月22日 21:43

物流管理機(jī)構(gòu)及政策分布概覽12月04日 14:10

盤點(diǎn):2017中國零售業(yè)十大事件12月12日 13:57

2017年中國零售電商十大熱點(diǎn)事件點(diǎn)評(píng)12月28日 09:58
